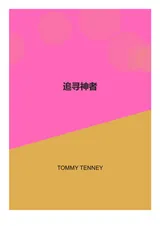关于本书
在《神秘学大师现归基督》一书中,艾克·内森·乌佐玛教授分享了他从高级神秘学领袖到寻求救赎并皈依基督教的个人历程。他描述了神秘学的黑暗世界,以及最终促使他放弃旧信仰、拥抱耶稣基督之爱的超自然遭遇。乌佐玛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信仰的力量以及转向上帝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
John Wesley

我们需要更多圣愚
一名男子被困在一辆汽车里,正从山坡上冲向悬崖。车门锁上了,刹车失灵了,方向盘几乎失灵。他看到前方很远的地方,其他车辆正飞速坠入深渊。他不知道它们坠落了多远。他们在底部发现了什么,他无法想象。 但他并不寻求了解;他也不试图想象。相反,他刷了刷挡风玻璃,爬进后座,戴上耳机。 这幅图片改编自彼得·克里夫特 (Peter Kreeft) 的作品,记录了我在 2008 年 1 月走在科罗拉多州一所大学的人行道上时的情景。汽车是我的身体;山丘是我的时间;悬崖是我的死亡。我和大家一样,急切地等待着脉搏停止的那一刻。尽管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还是找到了一千种方法来转移视线。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诗篇 14:2)如同许多其他人之子一样,我既不理解,也不寻求,既不祈求,也不敲门,只是任由自己在时间中翻滚,丝毫没有想过永恒。坦白地说,我是个“愚昧人”(诗篇14:1)。我迫切需要另一种傻瓜来叫醒我。 刺破白日梦 或许,很少有人会看着像我这样的普通西方人的生活——忙碌、成功、精神上漠然——然后说“愚蠢”。但这会不会是因为这种愚蠢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呢?我们现代西方的男女是否已经默默地达成了一项协议,无视永恒? “我们现代西方男女是否已经默默地达成协议,无视永恒?” 十七世纪的基督教博学者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就是这么认为的。当帕斯卡环顾他的现代国家、邻居以及自己时,他看到了一种集体病态,一种共同的疯狂:“人类对小事的敏感,对大事的麻木,是一种奇怪的紊乱的标志,”他说道( 《现代异教徒的基督教》,203)。 我们培养爱好,追星,阅读新闻,却不知自身为何而生。我们跌跌撞撞地穿梭于浩瀚无比的宇宙中,被无数错综复杂的奇观环绕,心不在焉,以至于无暇问一句:“这是谁创造的?”我们对政治有着坚定的看法,却不在乎灵魂是否永生,以及永生于何处。我们常常照镜子,却很少审视自己深邃而堕落的内心。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紊乱。 就这样,帕斯卡手拿针四处走动,试图刺破世俗或宗教名义上的冷漠白日梦,直到永远。他未完成的书 《思想录》(Kreeft 在其杰作 《现代异教徒的基督教》 中进行了删节和解释)可能是他最锋利的针。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 我们的生活被神秘与不确定性所包围。我们生活在浩瀚宇宙中的一块小岩石上。我们几乎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我们甚至难以理解自己。但有些事情依然清晰无误,包括我们终有一天会死去这个伟大的事实。我们的车飞驰而下,今天比昨天更低。万丈深渊在等待着你。 然后呢?对于像帕斯卡和我们这样的世俗或名义上信教的同胞来说,只有两种选择:“不可避免且可怕的选择:被消灭或永远受苦”(191)。要么基督教是错误的,我们摇曳的蜡烛将永远熄灭;要么基督教是正确的,我们太晚才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落入“愤怒的上帝之手”(193)。 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会让我们相信,八十年“过得很好” (无论它意味着什么)充满“个人意义”(无论它意味着什么)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我们无需再追寻更多。对帕斯卡来说,这句话出自一个把挡风玻璃漆成黑色的人之口。正确看待死亡,它就像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幕:它将手指伸回生命的各个角落,毁掉每一刻,黑暗中见证着一切都并不美好。 “最后一幕是血腥的,不管这出戏的其余部分多么精彩,”帕斯卡写道。 “他们把尘土扬在你的头上,这事就永远结束了。”(144)站在地上的洞口,站在尘土之上,我们来自尘土,也将归于尘土(创世记3:19),想想:“这就是世界上最辉煌的生命的终结。”(191)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谜,被包裹在一个神秘的世界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坟墓。” 我们自己是一个谜,被包裹在一个神秘的世界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坟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疯狂的“解决方案”,如此可怕的困境可能会让我们寻求智慧。 我们“解决方案”的疯狂 我们——凡人,濒临悬崖——通常如何应对自己的困境?“我们把一些东西挡在面前,不让我们看到它,然后不顾一切地冲向深渊。”(145)我们否认。我们转移视线。我们分散注意力。直到有一天我们死去。 当然,没有人会说:“我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我不想考虑我的死亡以及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潜意识里比这更压抑真相(罗马书 1:18)。我们本能地避开“丧家”,或者用委婉的说法来修饰它,因为害怕可怕而明确地面对“这是全人类的末日”——这就是 我们的 末日(传道书 7:2)。 Kreeft 总结了 Pascal,写道: 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你的生活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客厅地板正中央却有一个可怕的大洞。于是你用图案繁复的壁纸遮住这个洞,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结果你发现屋子中央有一头犀牛。犀牛象征着悲惨和死亡。你究竟该如何藏匿一头犀牛?很简单:用一百万只老鼠盖住它。多找些消遣。 (169) 八十年,或许看似很长,让人无法回避生死等最根本的问题。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八十年并不算长。成就一番事业,养家糊口,积累财富,计划假期,获得晋升,看看电影。收集体育卡片。阅读新闻。打高尔夫球。抵制令人不舒服的问题。 我们在悬崖边挂了一道帘子,使我们看不见深渊。但不要急于求成。 世界上最理智的人 我们选择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我们可怕的困境。分心之举让我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保持镇静,而不是让我们去寻找解脱。这意味着世界迫切需要像帕斯卡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借用教会历史上的一句话) 圣愚 。 术语 圣愚 与保罗在谈到“神的愚拙”(哥林多前书 1:25)并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 4:10)时所用的讽刺意味是一样的。事实上,圣愚是世界上最理智的人。他们感受到了罪恶和死亡的刺痛。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救赎。现在,他们正努力将救赎告诉世人。 他们与帕斯卡一同领悟到“只有两类人可以被称为通情达理:一类人因为认识上帝而全心侍奉他;另一类人因为不认识上帝而全心寻求他”(195)。因此,圣愚号召人们进入“愚昧”之中,而这恰恰是我们唯一的理智。 他们来到那些心烦意乱、迷失于歧途的人身边,他们服务、关爱、劝说、激励。他们冒着失去名誉和安逸的风险,甘愿在这个任性的世人眼中显得愚昧。他们将永恒带入与公园收银员、邻居和其他家长的日常对话中。他们勇敢而耐心,勇敢而仁慈地说:“看看你的死亡。看看你的罪。并全心全意地寻求他。” 对于那些一心想转移注意力的人来说,圣愚或许显得不平衡、极端、笨拙、咄咄逼人。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有些人听到这些傻瓜宣扬的基督,会感受到“上帝的力量和上帝的智慧”的光芒(哥林多前书 1:24)。他们将成为他的另一个傻瓜。 赐给我们更多愚人归向基督 帕斯卡(以及使徒保罗)让我感到,我尚未达到应有的愚昧程度。我常常宁愿选择社交礼仪,而非神圣的不适;宁愿选择世俗的美好,而非世俗的大胆。但他们也让我对我们身边的“圣愚”们心怀感激,并渴望更像他们。因为我欠一个人一条命。 2008 年 1 月,当我的小汽车冲下山坡时,我尽力遮住眼睛,有人在人行道上拦住了我。我后来才知道,他参与了一个校园事工,以向学生传讲耶稣而闻名——广为人知,但并不被人喜爱。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信息是愚昧的——他们在人行道上拦住别人的方式更是绊脚石。但那天,我蒙恩,这看起来就像是上帝的智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我各种各样的消遣都无法将我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活得精彩”的人生也无法赦免我的罪,也无法让我的坟墓重新被挖掘。只有耶稣才能做到。需要一个神圣的傻瓜才能让我恢复理智,哦,这个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的傻瓜。